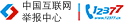人间
作者:nolix,德语翻译,音乐评论人,现居上海
你可能无法想象现在在上海市区内还存在不少租户,需要每天早上去倾倒便壶。但这在堆场旁的住户眼中很正常,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孩子与少许偕同他们来到上海港区打工的老年家属。
“地下室租户”里有不少女生
故事或许首先能从距我家门口不远的早点包子摊说起,这个包子摊是流动性的,因为不是在市区,所以不会有人驱赶。车里的后筐,放着总是热腾腾的包子,外面一层因为隔着泡沫箱而保暖性甚好。“包子阿姨”从五点多就开始售卖,也兼售一些豆浆与酸奶,生意不好不坏,司机与堆场工人去买得最多。我最初正是从她那里开始知道,港区周围数平方公里内散布着不少大大小小的租住区,价格低廉,而交通、购物环境也不差,其中就包括“地下室租户”。
我所谓的“地下室小区”,自然也是不得已的称呼,因为这样的小区可能本身就并没有名字。通常,那些曾经是厂区与办公楼的所在,小楼大小适中,改建后就成了多功能,二楼、三楼能租给那些迷你规模的货运及报关公司,一楼是房东自留,地下室则会租给来上海港口打拼的年轻人。
房东给的报价相当划算,我去过其中的几间,通风光线条件都很一般,此外房东还不得不配置价格不菲的进口除湿器,以便应付上海都市的梅雨季节,否则地下室简直就是南部洞窟的气息了。这样的出租,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毫无吸引力,唯独优势在于每个月的租金能压在千元以内——这哪怕在上海郊县都是相当划算的,重要的还不是会被罚的群租。
租客间,在附近港口或货运公司做抄单,报关等零碎工作的年轻人最多,在外贸公司做文案的也有一些,不过随着这两年外贸数量下降,港区的所有公司日子似乎变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好过。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18至25岁的年轻人会选择来这里的货运或仓储公司打工,一方面,入职要求门槛不高,一方面底薪还行,不需要像销售那样整天外面跑,还完全靠每一笔的提成。再者,假如公司不景气,他们隔天就转投隔壁的物流或者另一家快递,这儿的选择很多。
有时,这些员工会喜欢主动加班,呆在环境与温度条件都还不错的单位,必然不是出于对工作的单纯热爱,而是单位(特别是外资仓库)里做什么事都一应俱全,他或者她如果长期蜗居在地下室,对于身心无疑更不好。某一天,当我阅读起路内的《雾行者》,便非常理解为何主人公(仓库管理员)的心态和室内布置为何会是那样的奇怪。
予我意料之外的倒是,地下室住户里有不少女生,她们经常将房间打扫得非常干净清洁,装饰品一应俱全,甚至化妆台都肯花钱自己购置。据了解,她们的工作不在仓库,而是出门骑共享单车,先完成到地铁站这段路,然后去另一些单位上班,选择这样的屋子也是由于地理交通的优势。
对于这样的“地下室租户们”,他们的一日三餐毫无疑问是在外面解决的,因为这样的地下室租户既然罕有通风口,也就不太可能有灶台或可供摆放电磁炉的地方。当然,有的住户主动自己购置了小冰箱,但夏天放饮料用的情况多一些。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地下室租户没有优点的话,那就错了。它通常还配有一个独立卫生间,好的情况下有淋浴,抽水马桶一定有,除了需要去公共地方完成另外的事——例如可供投币洗衣。
旧楼改造房租户 每日倒便壶
那么,回到文章开始处,每日倒便壶的租户和“地下室租户们”又有哪些区别呢?位于堆场的西北侧,过去旧楼改造的例子里,光线、通风都好于地下室太多的,衣服更可在公共的敞亮院子里晾晒。这栋楼四层,在每层楼梯的转弯处,设有一个盥洗的位置(除了一楼之外)。所以如果你住在一楼的话每天一早首先会被二楼三楼拐角处洗衣服的嘈杂声音吵醒。自来水供应充足,所以人们露天搓洗衣物也都成了习惯,有些大叔顺着楼梯直接向下淌洗衣水,我也不知道这个习惯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总之石质楼梯倒是被冲刷得光洁明亮。
因为房间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去倒便壶,已经见怪不怪。一间房间有水龙头和洗菜的水槽,屋内可以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包括之前说的洗衣露台在内,这些都是比之“地下室租户们”的优点。
需要稍说明下的是,这些艰难的居住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在已超过四十五岁的叉车司机,或者资历丰富的堆场工人员身上。与每一个自信满满的长途卡车司机相似,经验丰富的堆场机械操作工人虽是标准的技术蓝领,也早已经在周围区域(甚至是学区)购起了商品房。
每当他们每次换下统一工作制服,穿上笔挺西装的时候,看起来和市区里出人头地的那些成功商人没太大区别,甚至还总是笑眯眯的,更乐观洒脱些,我会这样打招呼:“这一段活儿做完了是不是打算休息上好些个日子?”
他们随即也会满意地表示,不管是时间还是经济条件,出去旅游一阵子确实是好主意。然而,这类在堆场及仓库内部打工数十年的“蓝领专家”,毕竟总是少数。我所熟悉的大部分工人,也还都是先前提到的,改造旧屋的租住户。
把旧屋大院住出了工人大院的感觉
例如在我谈论的这个院子里,最早起来的人群是堆场或仓库的保安大叔,当然,衣服和帽子打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的他们,此时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用慢吞吞的电瓶车载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上学。六点多钟,曙色初明,看上去有点早,也只能这么办了,那是因为,他如此一路上就先可以“寄送”掉孩子,而后直接去接续堆场里上个人的夜班,免得空跑两回。我经常想,这睡眼惺忪、一头乱发的孩子是不是总是第一个到校的人,或者,比老师都早?
似有规律,在仓库附近做保安的,主要是四十岁以上的男性,而做清扫那些杂务的或在单位食堂里打零工的则是年纪更大些的女性。
我所熟悉的蓝婶,就是这么一位负责管理租住户中央大院的北方阿姨——谁派遣的差事倒不知道。她皮肤黑,有时看上去蛮严肃的,其他家小孩也不敢和她搭话,不过也正因为她的严格,所以大院的卫生一直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聊天中,她说因为自己是北方过来的,所以莫名其妙地特别喜欢上海所近乎无限提供的清水。她总是哼哼着小调(因为现在已经实行垃圾分类,是她负责)分类完垃圾,继而将长长的软水皮管从晒架上拖下来,冲洗那几个公用大垃圾桶,直到大院子里的地面上满是晶莹的小水坑,她便满意地收理工具,回屋去了。